报告文学连载:张扬与《第二次握手》罪案始末(3)
发布时间:2017-08-11 作者: 张扬
回顾:逃亡中写作《归来》

点击可观看视频

这段视频来自作者故乡河南省长葛市宣传部制作的专题电视片。
张扬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深情地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科学的春天,也没有自己现在的自由和幸福!
在上述第一次审讯中,预审员曾经问及我“有无前科”?
这是一个典型的“例行性”问题,对每个犯人都要问,在每份判决书中都要写入的。
他们喜欢有“前科”的人。这种人可以解释为“屡教不改”,从而“从严惩办”。
我大声回答:“有!”
这样回答不符合事实,却符合办案人员的胃口。那么,就让他们先高兴高兴吧。
《辞海》“前科”条:“法律用语。指曾经被法院判处过刑罚。”
我从来没有被任何法院或“文革”中取代了审判机关职能的各级“革委会人民保卫组”和“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处过刑罚”,因此从法律的意义上说并无“前科”。然而,“文革”中连法律本身都没有了,还有什么“法律的意义”?
但如果说在看守所中被关押过也算“前科”,那么,可以说我有前科。
我这“前科”怎么来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超大型政治运动。这场超大型运动中贯串着、交叉着无数大、中、小型运动;1970年春节后开始的“一打三反”是其中一场大中型运动。“三反”是些什么内容记不清了,好像是反贪污、反浪费什么的;这“三反”是陪衬,“反”些什么无关紧要,关键是那“一打”,全称是“严厉打击反革命活动”。
搞了多年“文化大革命”,“反革命”却越搞越多,于是就得严厉打击。到处都在开“公捕大会”“公判大会”,到处贴着布告,一批又一批“反革命犯”被判刑或处决。当时响彻云霄的口号是:“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新××(这××为地名,一般为县名或市名)!”
我在“一打三反”中也成了“反革命”,成了“逃犯”。来历是这样的:浏阳一中红卫兵组织“鲁迅公社”的头头,一个既敏感又偏激的“小将”,名叫罗孟寅,自1968年与我结识后成了朋友,彼此通过一些信。他受小说《牛虻》影响很大,崇拜作品中那位职业革命家亚瑟,在1968年给我的信件中猛烈抨击了“非神学的圣经”和“一神之下万人之上的蒙泰尼里红衣大主教”,扬言要“扬起无产阶级革命的巨斧,砍倒那林立的偶像”,等等。我回过几封信,表示同意和支持他的观点。
“林立的偶像”指“文革”中的个人崇拜狂潮,“林立的”也可以理解为“林彪搞起来的”;“一神之下万人之上的蒙泰尼里红衣大主教”无疑指那个号称“亲密战友”、位居“副统帅”的林彪;“非神学的圣经”指“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老三篇”、“红宝书”、“一句顶一万句”和“带着问题学毛著”等等恶性膨胀的教条主义和现代蒙昧主义;至于“扬起无产阶级革命的巨斧”,表示主张以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暴力来彻底否定“文革”!
凡此种种,在今天看来是多么普通,多么正确,多么富有政治远见!1976年10月的一举逮捕“四人帮”,就绝对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是做文章,而是一次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暴力,凭着这个暴力才得以在后来彻底否定“文革”——然而我们的议论在当时却是“大逆不道”,罪该枪毙好几次的。
我比罗孟寅大几岁,“老谋深算”一些,因此从来不保存别人的信件,包括他的来信,也提醒他不要保存我的信件。但他不听,居然保存了别人的一千多封信,俨然日后要当“导师”,出“全集”似的。其实他因偏激,一直是县里密切关注的对象。以他为首的“鲁迅公社”早于1968年春的“彻底摧毁省无联”运动中已被“摧毁”。
“一打三反”刚开场又抄了他的家,搜出成堆的信件,其中有我那几封。于是,他和他那些同学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统统抓了起来,关进浏阳县看守所。我因与他的同学们都不认识,自1968年以后与他本人几乎也没有来往,因此没有被算作“成员”,但也成了“反革命分子”,被迫逃亡。
我在长沙的青年工人中有不少朋友,他们了解我,同情我,节衣缩食冒着风险帮助我,掩护我。我不能回家,长期躲藏在简陋的工人集体宿舍里,这儿三天,那里两天,不断转移,疲惫不堪。一碗面条,一个包子或烤红薯,往往就是一顿饭。每当走上长沙街头,都得戴上大口罩,把帽檐压得低低的,像电影中的逃犯或地下工作者……
尽管如此,我却又写起了《归来》,走到哪里写到哪里。
作为知青,我一直穷困不堪,逃亡生涯中更加一贫如洗,连笔记本和稿纸也买不起。我弟弟的同学邹白沙送了一个黑胶皮笔记本给我。他知道我没有其他嗜好,只爱写作。我不喜欢一般稿纸,因为它“条条框框”太多,一页纸只能容下三百字,甚至更少;我也不喜欢那时通用的所谓“材料纸”,那种纸只印着一道道稀疏的横杠,也容不下多少字。我喜欢这种黑胶皮笔记本,开本较大,横杠细密,如果把字写小些,每页也许能容八、九百字或上千字,一个本本就能写多少万字,能完整地容纳一部中篇小说了……
逃亡中的我便用那个本本再写《归来》。在狗窝似的单身工人宿舍中写,在候车室的条椅上写,在乡村小镇旅店的昏黄油灯下写——每次多则写一两千字,少则写一二十字,写得很慢,很难,很累,但每天都要写一点。
1969年12月31日和1970年1月的最初几天,我是在汨罗县乡下友人家度过的,先到大荆公社一个山村,又到智峰公社一个山村。那几天滴水成冰,积雪盈尺。当地农民极穷,没有棉衣,在家烧木头取暖,不敢出门,孩子们竟赤脚在雪地上玩。大荆的友人徐鸣皋,是小学教师,独自教一所学校,全校只有一座茅草屋,屋内只有一间教室和一间供教师住的房子,还有一间厨房。所有这些屋子都狭小低矮。这么一个学校却有四、五个年级和二三十名学生;都坐在同一教室内,每个年级一行座位,徐老师轮流教每个年级。这种学校据说叫“复式班”。
尽管条件极其简陋,但毕竟是学校,所以徐鸣皋夫妇住的房间内居然有一张小书桌,我便时时趴在那桌上写作,连头都不抬。手冻肿了,脚冻麻了,我仍不停地写。
我的行为引起附近一位农村妇女的兴趣,悄悄向徐老师的妻子打听我的情况,说是这么勤奋刻苦的读书人今后必有出息,要把谁家一个怎样怎样标致的姑娘介绍给我。我听后淡淡一笑。这就叫勤奋刻苦?我今后还能有出息?——如果她知道我是个逃亡的“反革命”,不吓晕过去才怪呢!
在大荆住了两天后,我又走几十里山路到了智峰。
这个公社位于山区,交通不便,气温更低,积雪更厚,农民也更穷,我那姓兰的朋友也不例外;因为太穷,低矮阴暗的农舍中没有一张凳子椅子,墙上没有一个窗户,屋顶上没有一片明瓦,几乎是家徒四壁。但有一个高高的五斗柜,肮脏而破旧,靠黑糊糊的土墙放着,也许是土改时从地主家弄来的“胜利果实”。
柜上搁着几只大大小小的坛坛罐罐,还略有空余,能摆下我的笔记本。但柜高齐胸脯,又没有椅凳,于是我就站着写;站着还有一个好处,便是全身筋肉绷紧了,不那么感到冷。大雪天应该关上门才对,但我却让门完全敞开,任寒气冲卷而入;因为门外是一处陡坡,坡上厚厚的积雪可以将光线折射进来,我便靠借着那雪光写啊写的。
当然,不会不冷或不那么感到冷,而是冻得浑身索索发抖,双脚完全失去了知觉,双腿也在失去知觉,像是“飘浮”着。儿童时代看书,看到“囊萤夜读”、“凿壁偷光”之类故事,颇为叹服;现在才知道,人逼急于是什么办法都能想出来的,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在山上住了几天。回大荆又住一夜后,步行到京广线上的黄沙街车站,赶上一趟慢车。夜间回到长沙。身上没几个钱,买不起票,出不了站,被扣下盘问了好久。我声称在捞刀河(离长沙最近的小站)上的车,终于按这种最低票价办了补票手续,被放出车站。
掩护我逃亡的好心人很多。从汨罗回到长沙后,我住在市物资局新河碱库的青年朋友李桂秋那儿。新河是捞刀河注入湘江处一个冲积地带,位于城郊结合部,较偏僻,多仓库堤岸,有几条铁路专线。小李属于那种“少年老成”之人,性格内向,为人干练,对我很好。所谓碱库,是几只贮存氢氧化钾和氢氧化钠的大钢罐,外加两三排红砖小平房,一圈围墙。小李在碱库有一间屋,屋内有两张单人床,他和我一人一张。碱库人很少,没有食堂,工作人员到附近油脂化工厂食堂搭餐。
吃住都不成问题了,我便在那斗室中安心写作。“文革”期间经常搞“革命行动”,也就是在全城大肆查抄搜捕。一天夜里又要干这种事了。李桂秋出身城市贫民,“根红苗正”,是“依靠对象”,所有这些“行动”都不瞒着他。那天从油脂化工厂打饭出来,他望着匆匆来去的一队队、一车车戴红袖套的造反派和民兵,朝我笑笑:“快开场了!”
我感到自己是在“台风眼”里。周围狂风暴雨电闪雷击,满布恐怖和死亡,而这个小天地内却蓝天白云风和日丽。我知道这是假象,是暂时的,台风在高速移动,“台风眼”也在移动,压顶之灾的袭来只是时间问题……
真巧,我在黑胶皮笔记本中写完了《归来》,又在其最后一页写完了“后记”。因为没有框格,无法准确计算字数,估许有六、七万字吧,算个中篇小说。
小李读了《归来》,赞不绝口。他与我结识不久,是第一次读这部作品。
我过着动荡的生活,在长沙市区“流窜”,跟各种各样的朋友会面。我并没有什么“反革命”的图谋和活动,只不过在痛苦地消耗青春,打发时间。我想“文化大革命”不能永远搞下去,“一打三反”也顶多搞几个月,风头过去后我就回农村去,仍然当知青,干农活。除此之外,我不知道我们能有什么前途?
1967年夏季全国形势极度混乱,武斗猖獗,许多地方连枪炮坦克都用上了。我回到长沙,“闹中取静”,每天到烈士公园的凉亭中编纂《鲁迅语录》——当然,像我写小说一样,不是供出版,而是供自己和几个朋友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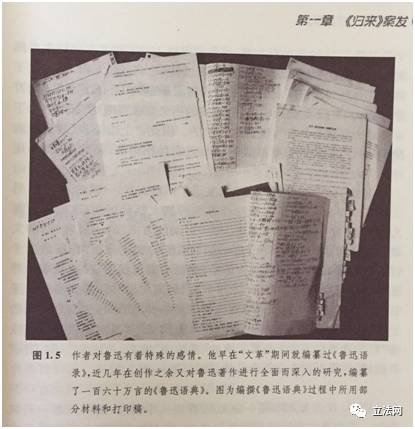
我一位名叫许九皋的知青伙伴在湖南一个知青群众组织当“司令”,他的“总部”里堆满了“上山下乡运动”的文件材料。他把我请了去,我利用条件便利仔细研究了那些文件材料,终于发现“上山下乡运动”的起因: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使人们不敢讲话了,主要是党外的人们不敢讲话,于是听不到不同声音,导致1958年的“大跃进”,对经济造成严重破坏;但党内还有人敢讲话,于是又搞了1959年的反右倾,导致1959—1962年的“三年特大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几乎崩溃,城市人口过剩——于是“上山下乡”成了解决这一系列严重问题的减压阀。湖南最早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于1963年,不是偶然的;一些地方的相关办事机构就叫作“上山下乡劳动力安置办公室”,就是这么来的。
因此,“上山下乡”跟革命和战争年代广大知识青年投身革命与工农兵相结合,跟所谓“青年运动的方向”根本不是一码事……
也就在这个1967年夏季,我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约五千字,另一篇三、四万字,占据了一张对开报纸的绝大部分版面;这后一篇题为《上山下乡运动是对毛主席“青年运动的方向”的彻底背叛》的文章论述严密,对“上山下乡”运动作了系统的理论分析,在政治上予以彻底否定,在社会造成很大影响,然而后来也成了我的“反革命罪证”之一。
特别是1968年毛泽东下达“最高指示”兼“最新指示”,千百万高中和初中学生无论毕业没毕业的一律“到农村去”,形成新的上山下乡高潮,我1967年发表的文章更构成了“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严重罪恶。加上与罗孟寅的“反革命”关系,一旦在“一打三反”中被捕,前程对我来说将会是非常凶险的……
那天,我去黄兴南路一家旅店看望一个朋支,随身挎着一只帆布包。我在逃亡中时时带着这只挎包,包中装着牙膏牙刷毛巾肥皂和最低限度的换洗衣裤,一叠“文革”中仍然按期出版但已经没什么人阅读了的活页报刊《科技参考消息》;眼下则还有刚刚写完的《归来》……
在从新河碱库去黄兴南路的途中,我忽然“心血来潮”,产生了不安或不祥之感,于是跨下公共汽车,走进火车东站。这是当时长沙两座火车客站之一,已经沿用了半个多世纪,专门停靠特快和直快列车,位于闹市区(旧址在今天长沙市芙蓉路与五一路交叉的立体桥处)。
这座车站很简陋,布局凌乱,站区内有铁路工人住的几排简易平房,我的知青伙伴陈富强住在那儿。我将挎包放在他家,空手只身前往黄兴南路。
半小时后,我的预感被证实了。公社公安特派员带着两名大队干部在那家旅店大门附近蹲坑守候。特派员是新来的,不认识我,因此需要带别人来指认。我被捕了。
自“文革”以来,我已经挨过不少整,受了不少批斗,算是“身经百战”了。因此,面对被捕,我很平静。
“预感”是很奇特的——不然,我不会中途走下公共汽车,将挎包放在陈富强家。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小动作”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也给中国当代文学增添了一段特殊的史实。
原文来源:立法网微信公众号
(立法网 觉林寺/编)



 立法文化
立法文化






 在线客服
在线客服 服务热线
服务热线 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
 top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