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连载:张扬与《第二次握手》罪案始末(21)
发布时间:2017-09-22 作者: 张扬
审讯室里,办案人员死死盯住我与舅舅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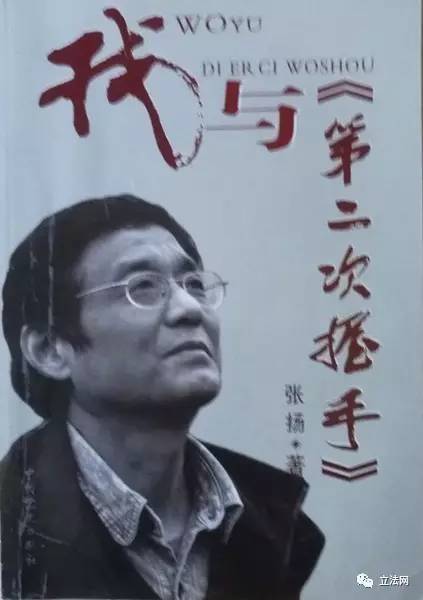
点击可观看视频

这段视频来自作者故乡河南省长葛市宣传部制作的专题电视片。
张扬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深情地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科学的春天,也没有自己现在的自由和幸福!”
我的舅舅、母亲和姨母都是知识分子。兄妹三人早年都受过高等教育,且都是正正经经的学校,不是“野鸡大学”,更不是“军警宪特”学校。兄妹三人都对政治不感兴趣——舅舅看来是有意疏远政治,母亲和姨母则是不懂政治,都没有加入过国民党和三青团。我母亲在陕西医学院时喜欢打篮球,于是三青团就来拉她说,入团吧,入了团就让你打篮球,多打球,还可以进球队参加比赛。我母亲一听,答道:“我即使从今不摸篮球了,也不加入三青团!”
她后来对我说:“我也不是有什么政治觉悟,我就是对那些东西不感兴趣。”
兄妹三人不加入国民党三青团,也没加入过任何党派社团。母亲和姨母倒是差一点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革命队伍。那是成荫被我外公拒绝之后,一气之下跑到武汉大学去读书,又随侯外庐赴延安。他写信邀我母亲和姨母一起去延安。姐妹俩不懂政治,但懂得延安是什么地方,愿意跟他一起去。秘密通过封锁线的时间限制极严,地点在山西境内什么地方。姐妹俩乘马车迟到了一点,那一批革命青年已经穿过封锁线到那一边去了;这次“失之交臂”,改写了姐妹俩一生的命运。
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和审干中,搞了许多“杠杠”,如国民党“军警宪特”呀,“反动党团骨干”呀,“反动会道门骨干”呀,“四类分子”呀,“五类分子”呀,“二十一种人”呀,等等等等;用那“杠杠”一量,就知道你的“敌友我”。然而用尽了那些“杠杠”,仍然无法将我的三位亲人划到“阶级敌人”一方去。当然,“主审官”把他们划为“麻雀”;而1958年全国有个“灭四害”运动,“四害”指蚊子、苍蝇、老鼠和麻雀。但是,“四害”灭得了么?另外,“四害”之中的麻雀很快获得了平反,说麻雀是益鸟,麻雀被捕杀后各种害虫急遽增多,等等。
当然,“麻雀”是一种比喻;这种比喻倒不说明“主审官”的文化素质低下,而是暴露了某些习惯于用人血染红顶戴的政法干部在那个年代形成的残害无辜、草菅人命的恶习。
1970年2月我被捕后,“捕快”们从我在某工人宿舍一个藏身处搜走我两个影集,其中有我精心收集、整理的我们家庭的大量照片。现在,影集移交给了省公安局,“主审官”在审讯室内当着我的面翻看它们。我知道南京时代的照片显得很“气派”,很像“资产阶级”,很使今天的“无产阶级”办案人员看不惯;但是,看不惯就看不惯吧,依据这两个影集不仅不能“定案”,也不能给我家定阶级。
没有政治历史问题,也没有“现实表现问题”。自1949年以来搞了无数次大小政治运动,兄妹三人都没有出过事,其中甚至包括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

至于他们跟《归来》的关系,则前文已有详细叙述。根据那些事实要把他们当作“麻雀”绑在同一根绳上并一齐掐死是很困难,简直是做不到的。但是,“主审官”决心“知难而进”。
在审讯室里,他死死盯住我与舅舅的关系。
我老老实实回答他的问题。
说实话,那时人口流动少,连电话都是很稀罕的东西;舅舅一家在北京,我们在长沙,除写信外没有其他联系方式。
我读高中时学俄语有困难,舅舅给我寄过俄语工具书和参考书。
姨母身体不好,却又吸烟很凶。我写信告诉舅舅,他写信劝幺妹戒烟,并寄了一点钱给她买营养品。
我母亲一位同事患青光眼,母亲嘱我写信问舅舅,北京有没有治疗这种眼疾的地方?我写了信,舅舅回信说,目前世界上均无治疗青光眼的有效办法;北京同仁医院是全国眼科水平最高的医院,但亦无法根治青光眼……
长沙岳麓山有一片古枫林,据说毛泽东青年时代常来此读书。我将一片枫叶寄给舅舅,说毛主席在这棵树下读过书。舅舅为这事给我回信表示谢意——从这事看来,他不仅不“反动”,还很“革命”呢;对他这么一个不谈政治的知识分子来说,至少算“进步”吧。而且这是他给远方的外甥写信,不是做给“组织”上看的。
上帝呀,还有什么呢?
即使在主审官的“麻雀”出口之前,我也知道他想干什么;然而即使我想帮助他,也无从帮起啊!
“在北京,你跟你舅舅都说过些什么?”
对了!尽管舅舅每天上班,回家后话也不多,但我们之间还是有过一些对话的。
一次,我问他:“你们做过中药有效成份的提取、分析工作吗?”
舅舅答:“这方面的工作很少。”
又一次,我问:“你们的工作中运用数学多么?”
他答:“用不着很高深的数学。”
——涉及科学和专业的话题,仅此二次。
虽只二次,却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即我对科学的关注。中医药是世界上一枝奇葩,但许多机理无法解释;在我看来,运用现代科学手段对其进行研究探索,是解开中医药奥秘并使之跨入世界医药卫生科学之林、更好地服务于全人类的好办法。此外,长期关注科学技术的发展动态,使我越来越意识到数学在所有门类的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甚至包括某些社会科学和哲学)中的重要的乃至是关键性的作用;我甚至认为,运用数学越广泛、越高深的学科,越够格被称为“科学”。而据我所知,除数学(纯数学和应用数学)本身外,运用数学最多的是天文学、力学、物理学和许多门类的技术科学,其中,力学和天文学的某些分枝甚至可以说本质上就是数学,而运用数学最少的近代科学是化学和生物学。舅舅所从事的药物学研究,本质上是化学,所以我向他提出了这么个问题。而他的回答也没有出乎我的意外,没有脱出我对科学的理解和掌握范畴。
与舅舅之间还有一段我从来没有对人谈起过的对话。
那一次,我们谈起原子弹,谈起“曼哈顿工程”。舅舅似乎想了想,简短说道:“有一位当时留学美国的中国女物理学家,参加过‘曼哈顿工程’……”
关于这个话题,他戛然而止,不再往下说。我也不追问。舅舅是个不苟言笑的人,他不说的事你最好就别问。但他终归是个科学家,说出来的话就肯定是有根据的。
舅舅是教授。抗战流亡期间也在大学任教。但是,抗战之后教育事业凋蔽,而毕业于美英教会大学的他本来认识很多美国人和英国人,又能说一口非常流利的英语,于是四十年代后期曾在南京的外交界任职。我估计,他就是在这一段时期获知“有一位当时留学美国的中国女物理学家参加过‘曼哈顿工程’”的——当年谈到这一点时,我和舅舅都很“低调”,平缓;但是,他这句极其简短的话却给我很深的印象和极大的震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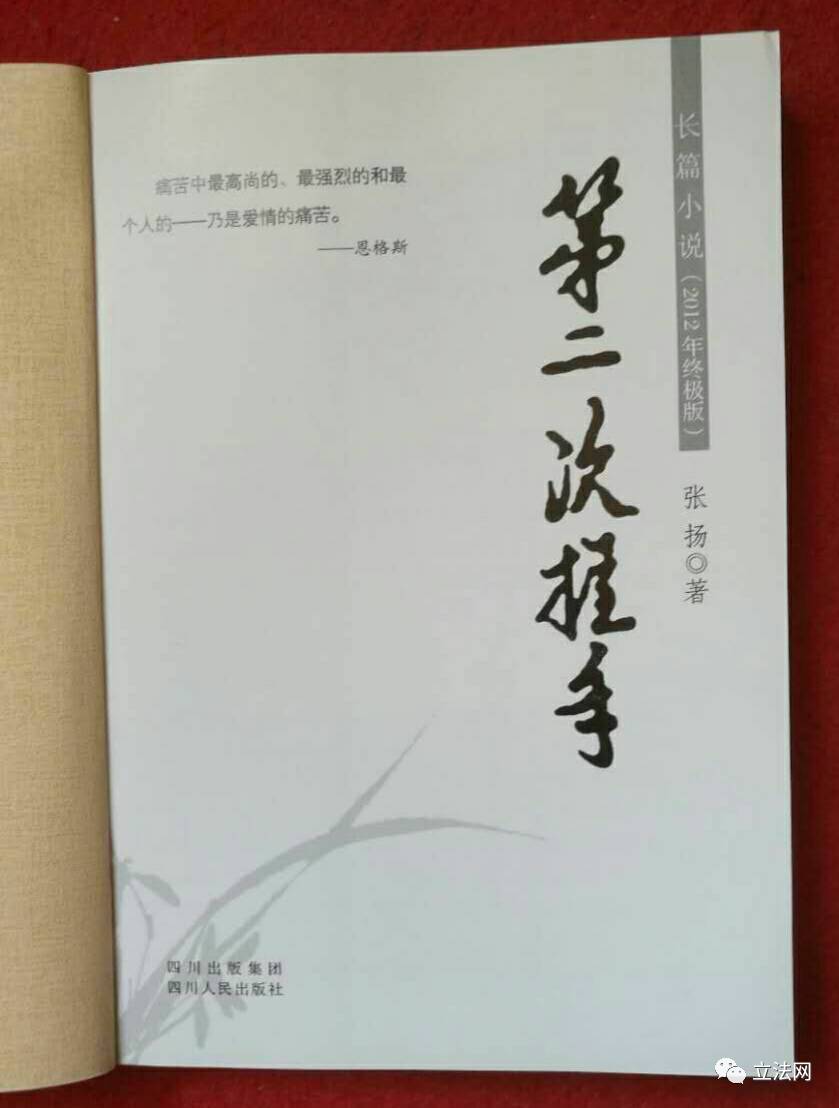
从《浪花》到《归来》再到《第二次握手》,作品中那位参加过“曼哈顿工程”的“丁洁琼”的形象,跟舅舅那句极其简短的话直接相关。
那个年代以“阶级斗争”为职业的人,往往形成一种“职业病”,即捕风捉影,草木皆兵,把一切都想象成或假设成“阶级敌人”的险恶用心和破坏行径,然后百计锻炼周纳,不择手段加以“落实”,给人定罪。譬如《归来》写新中国建国初期,美军在朝鲜战场上使用细菌武器,苏冠兰教授等在金陵药学院参加了我方为反对细菌战而进行的科学实验。这本是一段很寻常的描写,写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怎样开始参加革命工作,认识美帝国主义反人道的本质,等等,在情节上也有铺垫作用。但办案人员竟看出“特大犯罪”来了,说是我故意泄漏“我国从事细菌武器研究”的秘密,妄图借此诬蔑、丑化、攻击中国共产党,“企图扇动全世界都来谴责新中国”。
《审讯笔录》中记着与我的问答:
问:……是不是这样?
答:(不回答)
真的,我怎么回答?怎么回答都是白搭,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细菌战与反细菌战是对立统一的。不掌握细菌武器本身几乎是无法进行反细菌武器研究的——他们就是这样想当然地进行“推理”和办案,一步步把我往死路上逼。他们最大的“想当然”是认为我舅舅在那种单位工作,显然与细菌武器研究有关,因此很可能向我透露过这方面的机密。为此,他们在审讯室里和两次批斗会上对我轮番轰炸,大搞逼供信,但始终没捞到任何东西,因为根本就没有那种事!
当时的中国,落后到没有复印机。最先进的技术仍是照相机。于是,他们从审讯笔录和我的书面交代材料中挑选了一些与我舅舅有关的页面,拍成照片,派人到北京,找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要求他们予以支持配合,“深挖黑后台”。
这时已经是“文革”后期,各单位“军代表”早就撤了。但药物研究所的军代表高学增因为人品很好而破例脱掉军装留了下来。他对湖南省公安局派来的人嗤之以鼻。八十年代初期,高学增同志将那批“档案照片”全部送给了我。
原文来源:立法网微信公众号
(立法网摘编)



 立法文化
立法文化






 在线客服
在线客服 服务热线
服务热线 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
 top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