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连载:张扬与《第二次握手》罪案始末(9)
发布时间:2017-08-25 作者: 张扬
“主审官”没对我动过肉刑

点击可观看视频

这段视频来自作者故乡河南省长葛市宣传部制作的专题电视片。
张扬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深情地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科学的春天,也没有自己现在的自由和幸福!”
在审讯中,我交代于1963、1964、1967和 1970年共写过四稿,加上1974年稿,先后写过五稿《归来》。
因为以“无罪辩护”为前提,所以我把这五稿写作的时间、地点和借阅对象等大体上都讲得很清楚。但实际上,自1963年以来我自己都记不得写过多少稿。反正每写成一稿便借给别人,别人又借给另外的别人,终至收不回来,只得又写;有时也因为自己觉得写得不够好而重写——这后一种情形还挺多,因为我从来没有对写成的《香山叶正红》或《归来》满意过,老想再写,企图使之至臻完美。但这个目的怎么能达到呢?即使是后来正式出版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我也很不满意,而且越到后来越不满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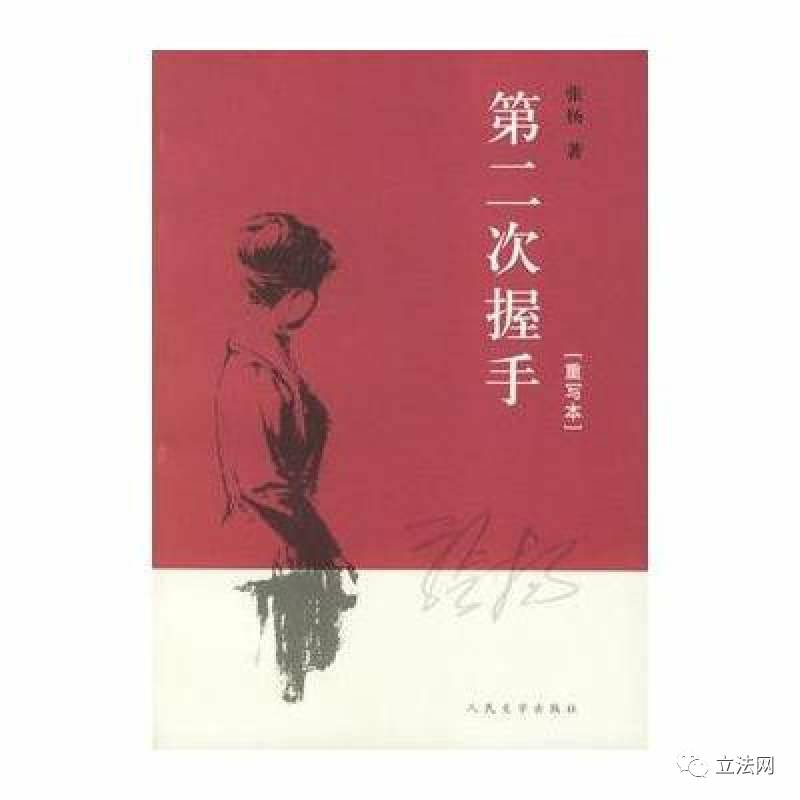
《香山叶正红》改名《归来》是1970年事,那一稿造成全国规模的传抄,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这一稿较短,只有五、六万字,传抄起来比较方便。
“文革”至1970年已经折腾了四年,对文艺的“围剿”从1964年算起则已达六年,中国的文艺领域已经“革”得光秃秃的了,御制的八个“样板戏”即使据说也有“艺术性”吧,但强迫八亿人连续几年尽看这些玩艺,唯一效果肯定是只能令人作呕。我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我深知《第二次握手》还很不成熟,瑕疵甚多;但我至少敢于自信地断言,它之所以受到群众的欢迎,是因为它在相当程度上突破了“四人帮”的禁区,表达了人民内心的爱憎!
正是因为“四人帮”搞得百花凋零,文艺园地中一片荒芜破败,才使得这部拙劣的作品得以呈现出一点特殊的风姿,引起人们的注目。
从这种意义上说,不是别人,而正是“四人帮”的法西斯文化专制,才帮助了《第二次握手》的大规模流行。这是多么冷酷而又多么公正的辩证法!
我说写过五稿,预审人员们在“定罪材料”中认定为写过六稿。他们知道不止六稿,但能证实的只有六稿,那就六稿吧;在他们看来,反正够杀我的头就行!
应该指出,即使在“文革”期间,正式的公安机关和公安干警,相对而言还是具备了较多优点的。
譬如无论在浏阳县看守所或省公安局看守所,对犯人都是不施肉刑的,哪怕对“气馅嚣张反动已极”不守监规且不断“谩骂”他们的我,惩戒措施一般来说也只是单独监禁或戴手铐,对我的长期绝食也只是几个彪形大汉将我五花大绑在一把椅子上,用铁棍钢钳撬开嘴巴强行灌食,直搅得我满口流血,差点呛死。
但我今天愿意对此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也得听命于人,不能让犯人真的饿死。许多人绝食是假的或半真半假的,我却是真的,最长的一次绝食长达十四天。
十四天后,身体极度消瘦羸弱不难想见,可居然还能走路,还能正常思维和语言,但全部牙齿大幅度松动,都快脱落了。
我还应该“感谢”他们,因为如果我绝食而死,也就没有以后的《第二次握手》,没有作为作家的我了,中国大地会因此少了许多浩然正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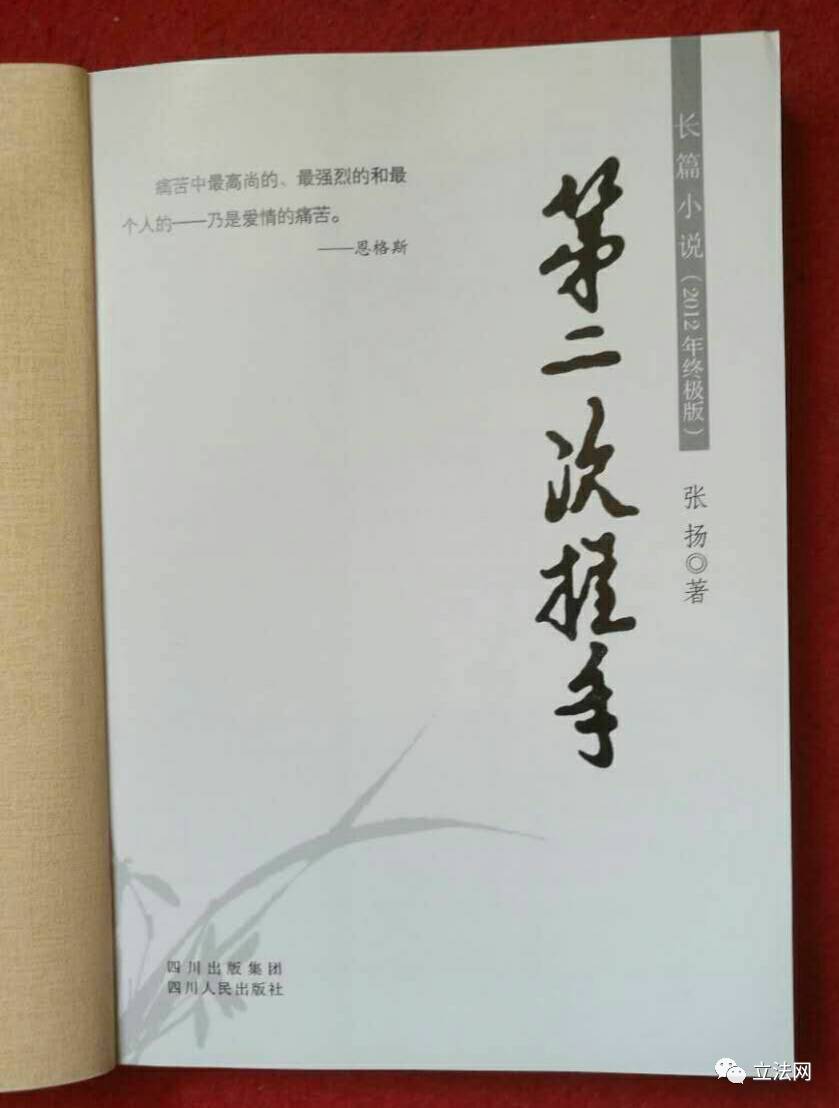
但我得声明,我所说的不施肉刑只是就我所亲历的两所“国营监狱”而言,其他监狱就难说了,至于当时大量的“群众专政”机构的滥施私刑酷刑,则是众所周知的事;此外,不施肉刑一般来说只是对政治犯中的思想犯良心犯而言。
原因很简单:肉刑对他们不起作用。对某些刑事犯和某些狂乱的犯人就不同了。不过总的来说那时的社会风气和党风政纪比现在要好;今天的所谓“牢头”、“狱霸”和这类犯人居然经常在牢房中打残打死其他犯人的事,那时是根本不会有的。
五官端正的“主审官”往往被我激怒。一旦激怒,其五官就不那么端正了,气血上冲,面如猪肝,圆睁双眼,凶相毕露,吐出一堆蠢话来,不但于事无补,反而给他自己下一步的“工作”造成被动;但一般情况下他总还是能满脸笑容(我称之为“职业性的假笑”),和颜悦色,温言细语,“谆谆善诱”的。
他从来没对我动过肉刑,从来不曾对我拍桌子打板凳,也很少大声喝斥威胁。相反,他经常引经据典,充分“摆事实讲道理”,也经常对我讲“政策”。
可惜因为他文化水平低,往往满口错别字。譬如有一次他劝我别学苏联青年的坏样子,说苏联变“修”跟青年一代变坏有直接关系。我问苏联青年是怎样一种“坏样子”?他说他们普遍严重“凶(酗)酒”。
其实我在牢房中连饭都吃不饱,骨瘦如柴,哪里有酒可“凶”呢?他还要我别学另一个“反革命犯”的坏样子,那人姓名中有一“铿”字,他念成“坚”。此外,他最经常的一个口头禅是告诫我不要“伟(讳)疾忌医”……
我算了算,这位“主审官”在“教育”我时,前前后后读错用错的字竟有二十余个。于是我写了一首打油诗,将那些错别字都嵌进去奚落他。
我还给省公安局党委写报告,说你们不是算我“文化犯罪”吗?不是指我“流毒全国”吗?“文化犯罪”而能“流毒全国”,说明我虽然政治上很反动但文化上很不错嘛!那么你们就应该派一个识字较多的预审员出马才对嘛!让这种半文盲来对付我,一派胡言乱语,不是贻笑大方,丢“无产阶级专政”的脸吗?
除识字水平外,“主审官”的逻辑、文理也很成问题。譬如当时有个政策,叫作“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主审官”洋洋得意,不下一百次向我宣讲此项政策,让我懂得我的“口供”无关紧要,我讲不讲或承认不承认都没关系,他们反正会用他们弄来的“证据”证明他们想证明的一切的。
他们是怎样搜罗“证据”的,下文再谈;现在先谈“主审官”的“重证据,不轻信口供”。
无论作为政策或话语(哪怕是“文革”期间的政策和语言),这种说法本身都没有错;然而一到“主审官”那里,便驴唇不对马嘴起来。譬如他一字一顿教诫我:“你听懂了吗?一个‘重’,一个‘不轻’——嘿嘿,这是有区别的咧,党的政策是很讲究的咧!”
我在给省公安局党委的一封信中写道:“在中国的语言文字里,‘重’与‘不轻’有什么‘区别’?‘重’就是‘不轻’,‘不轻’也就是‘重’。因此,把‘不轻信口供’分解成‘不轻——信口供’也就成了‘重信口供’或‘重口供’——如此逻辑混乱,语无伦次,连常识水平都不具备的人竟被派来审讯我,真是斯文扫地,成何体统!”
当年许多事,可以说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们确实做了不少坏事,伤天害理无中生有的事——效命于“四人帮”,就从根本上注定了非做坏事不可!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做了一些“调查研究”,搜罗到一些“证据”。其中最功德无量的,是他们根据我的“交代”出去“外调”,居然找回了好几种当年流向四面八方的我的手稿原件,其中包括最重要的、“流毒全国”的1970年稿!他们在审讯室中就不止一次非常得意地向我展示他们的这些“战利品”。
当然,他们苦心孤诣搜罗来那么多原稿是为了“重证据”,用这些“证据”来证明我在漫长岁月中怎样顽固坚持“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的,以便扎扎实实把我送上断头台;但是,这也揭示了事物的另外一个方面。
我原以为,经过那么漫长的岁月,经历了无数次政治运动,经历了“文革”初期排山倒海似的“破四旧”,手稿又从千百人手上传过,一定早就破损、毁坏殆尽了吧?
我做梦也没想到,相识和不相识的人们倾尽了他们的能力和爱心,小心翼翼地珍惜这部手稿,冒着风险保护她,直到云开雨霁,直到阳光重新普照大地!
原文来源:立法网微信公众号
(立法网摘编)



 立法文化
立法文化






 在线客服
在线客服 服务热线
服务热线 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
 top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