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连载:张扬与《第二次握手》罪案始末(27)
发布时间:2017-10-06 作者: 张扬
《归来》是鸦片,《少女的心》是砒霜!

点击可观看视频

这段视频来自作者故乡河南省长葛市宣传部制作的专题电视片。
张扬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深情地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科学的春天,也没有自己现在的自由和幸福!”
审讯室中经常发生的辩论,给我一种“秀才遇见兵”的感觉。
“主审官”正言厉色地问我:“你明明知道不准写爱情了,为什么还硬要写?”
他妈的什么权威机构在什么时候规定了“不准写爱情”了呀?
“我明明不知道‘不准写爱情了’!”我答。
我反问:“建国以来所有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革’以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名义或其中一两家、两三家名义发布的所有文件、布告之中,哪一条哪一款规定了不准写爱情?”
——即使在“文革”中,无论前期以各级“革委会人保组”和“公检法军管会”名义还是后期以各级人民法院名义发出的判刑布告,每一条判决都注明“依法”,包括对张志新烈士的死刑判决书。
从来没有一个判例声明自己是“非法判决”“枉法判决”“不依法判决”“依某某首长批示判决”“依不成文法判决”或“依某某判例判决”;而所有这些“依法”,“依”的可以是“文革”前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也可以是“文革”期间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或其中某一两家、两三家名义发布的通知、通令、条例和布告之类。
所有这些文件,特别是“文革”中发布的东西,往往相互矛盾,但并不妨碍它们在当时司法实践中的运用。
如“文革”中的《公安六条》,规定凡攻击林副统帅的人一律按现行反革命论处;但林彪自我爆炸以后这一条就完全颠倒过来,凡吹捧林彪的人一律按现行反革命论处。
尽管如此,运用起来并无不便,且仍算于“法”有据,不过是林彪出事以前一种处置方式,林彪出事以后截然相反的另一种处置方式而已。
但不论怎样,必须在公开或不公开的文件中有适用的规定,不然即使在“文革”期间,也不能叫作“依法”。“不准写爱情”即其一例。
翻尽建国以来所有可供作法律依据的文件,都没有这一条。预审人员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不说我违犯了法律,而指我违犯了据说是我“明明知道”的什么东西。
有时,我真为那些装腔作势审讯我、批判我的人感到悲哀。荒唐绝伦的“文革”和那些极左的东西,把他们腐蚀、愚弄到了何等地步,好像都变成了白痴。
我曾质问过“主审官”:看样子你四十多岁吧?那么,你肯定结了婚,而且跟你老婆不是包办婚姻,而是自由恋爱结的婚;你们的孩子大约也在十几岁至二十来岁之间,也快进入或已经进入婚恋时期了。你恋爱、结婚、生儿育女;你的子女又要恋爱、结婚、给你添孙子了,怎么你不是“反革命”?

当然,怎么说理也是白搭。狼要吃羊时,道理总是在狼的牙缝里。然而他们是狼,我却不是羊。斗争越往后越激烈。我与他们经常发生辩论,这种辩论总是在很低的水平上进行。譬如:
“你的《归来》是宣扬‘爱情至上’的’!”
我答:“爱情不至上,难道封建包办婚姻才至上吗?”
他们骂我“诡辩”。我道:“马恩列斯毛,哪一位伟大革命导师没有经历过爱情?你们自己没经历过吗?全人类都少不了它,说它‘至上’我看也不过分。”
他们正言厉色:“你的《归来》是鼓吹‘科学救国’的!”
我回答:“科学不能救国,难道只有愚昧落后才能救国吗?”
当然,又骂我“诡辩”。他们一拍桌子:“谁说了愚昧落后才能救国?你不要血口喷人。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科学吗?”
他们又噎住了。但眼珠一转又来了:“你笔下的丁洁琼并不爱国,她不是因为爱国才归国的!”
“那么她是因为什么才归国的呢?”
“因为爱情!她与苏冠兰的爱情,她回来找苏冠兰的。”
“丁洁琼爱国,也爱苏冠兰。就像你吧,你爱毛主席,爱共产党,但也爱你老婆和子女——二者并不矛盾,党章和法律都不能要求你只爱毛主席和共产党而不准爱你的老婆和子女。”
我侃侃而谈,“作品中的丁洁琼是具备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基础的。她的父母都是革命烈士,她的老师凌云竹也是个长期同情、支持共产党人的爱国者和进步人士,在丁洁琼赴美留学前还谆谆告诫她,千万不要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将来学成之后一定要回到中国来,把才学和本领献给自己的人民……”
“这一切统统是你捏造的!”
现在轮到我噎住了。
看来,我得把丁洁琼写成军统少将,潜回大陆从事破坏,被抓住了,跟我同案受审,才不叫“捏造”,才算“艺术构思”……
“你笔下的丁洁琼是杀人犯!”
“叛特资”“反动学术权威”和“地主资产阶级少爷小姐”已经不够用了,“杀人犯”也出来了。
我望着他们。
“丁洁琼帮助美帝国主义制造原子弹,用来干什么了?”他们瞪着我。
“用来打击日本军国主义呀。”
“打击了哪个日本军国主义分子?”
我一想,真的,自裕仁天皇和东条英机以下,确实没有听说哪个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死在原子弹轰炸中。就算在广岛、长崎可能死了一些日军官兵,我也拿不出一份花名册的;而且那些人算不算得上“军国主义分子”,也还是问题……
他们得意了,一拍桌子叫道:“丁洁琼造的原子弹都炸死了谁?几十万无辜的日本平民嘛,你说这不是杀人犯又是什么嘛!”
我望着他们,无言以对。真的,面对这样一些对手,我还能说什么呢?“丁洁琼造的原子弹”没炸准,办案人员造的“原子弹”却炸准了,搞得我哑口无言。
“你笔下的中国老一辈科学家全是帝国主义给培养的!”
“中国老一辈科学家不是帝国主义培养的,是谁给培养的?慈禧太后,还是袁世凯?”我回答,“帝国主义为什么要为中国培养科学家,是另一回事;但中国老一辈科学家确实是‘帝国主义’给培养的——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
我指出:由于长期的封建闭塞和反动高压,中国本土当时确实不可能自己产生近代科学技术和相关的人才。
他们已经把我与刘少奇挂上了,犹嫌这“专政”还不“全面”,又将我与林彪挂上。林彪“称天才”,他们也算我一个“称天才”:
“你笔下的科学家,全是凭他们的天才取得成功的!”
我反问:“什么叫天才?我认为天才就是某一方面比较聪明。我笔下的科学家们确实是凭聪明取得成功的,这有什么不对吗?不凭聪明凭什么呢,凭愚蠢吗?凭愚蠢也许可以到你们这里当预审员,但决不能当科学家。”
他们问我:“你自己说说吧,你的《归来》中写了一个工农兵吗?”
我想了想,《归来》中确实没有写一个工农兵。苏冠兰读大学时有个在学校看门的老申头,但那显然算不上“工农兵”,顶多算“劳动人民”,搞不好还可能算个“流氓无产者”。
鲁宁干过地下工作,在解放军中当过高级干部和军代表,但已经被他们划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不过我又一想,要他们“承认”什么?他们有什么资格承认不承认的?我跟他们是对立关系和敌我关系。他们用手铐、监狱对付我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我写《归来》就是为了跟他们那一套对着干。我从来没有承认、没有接受过他们“写工农兵”的主张和他们对“为工农兵服务”下的定义。
真照他们那一套办,该怎样对待他们所谓的“工农兵”出现以前的全部人类历史和人类文明?
不错,他们搞了八个“样板戏”,但那行吗?就算把“样板戏”发展到十八个,八十个,也不行!
因为这些东西的使命就是扼杀和取代千千万万真正优秀的文艺作品和人民群众自由从事文艺创作的合法权利,这些东西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虚伪;它们本来是为某些人装点自己“最最革命”的假脸和为他们逐步篡夺最高权力服务的,因而与人类正常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感情根本不相通……
但我不能把真实的“立场世界观”摆出来,于是反问:“法律规定了每个文艺作品要写百分之几十几点几的工农兵?怎样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才算纯正的工农兵?不是说‘依法’吗,很好,你们拿出具体的法律依据来!”
当然,他们不会拿出法律依据来,因为拿不出来,也无须拿出来。“四人帮”吭一声就是“法律依据”,就是他们的“圣旨”。
他们问:“你看过《少女的心》吗?”
“看过。”
“你看法怎样?”
“我没有‘看法’。”
“怎么会没有看法呢?”
“为什么一定要有看法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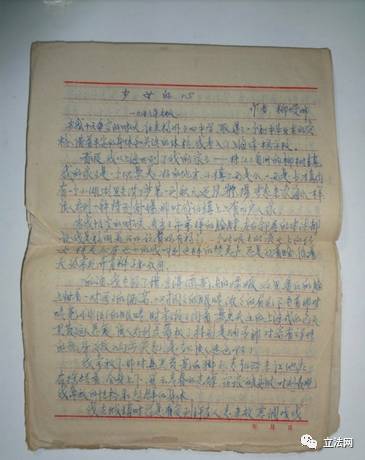
《少女的心》也是一部手抄本。用当时的观点看,这是一部纯粹的淫书;按九十年代某些论者的观点,则属于“性文学”,是“文革”期间青少年精神压抑的产物……
他们大声宣布:“《少女的心》是砒霜,《归来》是鸦片!”
我没作答,因为没必要作答。
他们叫嚷:“你的《归来》不是爱情不说,而是政治小说!”
我仍然没有作答,仍然因为没必要作答。这句话反映了他们所能达到的最高认识水平,还代表了他们所能达到的最高语言水平,亦即他们所能说出的最漂亮的语句。
世界上没有纯粹的“爱情小说”,所有爱情小说都是通过爱情反映社会,无一例外,《归来》也不应该例外。
问题只在我这小说写“政治”写得怎么样——他们和他们的后台老板认为写得很坏,“反党”;而我认为写得很好,绝大多数读过它的中国人也认为写得很好,写出了人民的愿望,也写出了正常的人性和感情。
“主审官”教训我道:“什么叫‘自强不息’?这不是我们共产党的话咧!”
1969年底至1970年初我逃亡时,宋承禹先生一面竭力帮助我,一面多次以“自强不息”鼓励我。
蒋介石到台湾后确实以“自强不息”为部下鼓气,这是从《参考消息》上可以看到的,并非我“偷听敌台”的结果;而宋家又出过宋希濂等几位国民党高级将领。
于是在“主审官”看来,“自强不息”就成了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专用话语”,共产党不能用,大陆的中国人也不能用,谁用了谁就是“反革命”。
其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一句著名的古语,出自《易经》;用今天的话来说,大意是“历史潮流滚滚向前,有志气者要坚持奋斗进取”
——像这样的语言,本身是没有阶级性和政治倾向的,谁都能用;当然,悲观厌世终于自杀的人不能用,此外,缺乏文化教养而又居心不良者最好也别沾边,免得丢“我们共产党”的脸!
我当面痛斥“主审官”搞资产阶级专政时,他的回答是“阶级敌人总是要把无产阶级专政诬蔑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在他看来,只要先把对手定性为“阶级敌人”,就什么都好办了。其实就他的所作所为而论,他才更像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
我1961年10月发表的处女作《婚礼》,是一篇反对封建思想、赞美新社会的散文。现在他们叫嚷:“你的《婚礼》也有问题咧!”显然,这些家伙因为长期捕风捉影,心惊肉跳,已经有些神志不清了。
……
总而言之,正如前文所说,辨论经常就是这样在很低的水平上进行。经常需要给他们纠正错别字,经常在一加一等于二还是等于七,以及太阳每天究竟是从东边升起还是从西边或北边升起之类“问题”上跟他们喋喋不休,简直无聊之极。
加之“四只麻雀”之类既险恶又愚蠢的说法令我吃惊,也令我厌倦和憎恨,后来根本不愿再跟他们对话了。于是“主审官”道:“你就是一个字也不讲,我们照样要把案办到底!”我说:“那你还跟我谈什么?”他说:“这是要看你的态度嘛。”
据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态度”决定一切。
我冷笑:“我的‘态度’你不是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吗?”
原文来源:立法网微信公众号
(立法网摘编)



 立法文化
立法文化






 在线客服
在线客服 服务热线
服务热线 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
 top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