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立法史上最早谴责酷刑的人是谁
发布时间:2021-01-25 作者:
酷刑成为处理疑难案件的常规方法,特别是在迫害巫师的行动中,苏格兰的做法酷烈至极,远超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酷刑被推向可怖的残暴之巅,远远越过了其他各地对它的限制。
酷刑逼供,始于罗马法,却最终深植于苏格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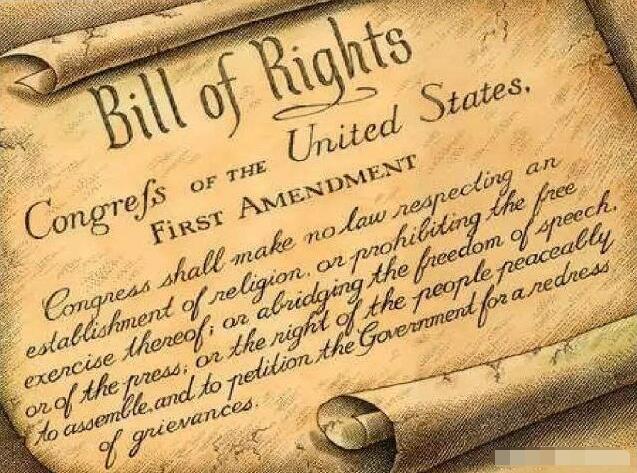
酷刑成为处理疑难案件的常规方法,特别是在迫害巫师的行动中,苏格兰的做法酷烈至极,远超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酷刑被推向可怖的残暴之巅,远远越过了其他各地对它的限制。
1652年,当英格兰的司法事务特派员们坐镇爱丁堡时,在被带到他们面前的刑事罪犯之中,有两名已经在苏格兰教会(the Kirk)面前供认过自己罪行的巫师。
他们是六人一组的余孽,另外四个人死于刑讯逼供之下——比如手绑于背后,再拎着拇指吊起、鞭刑、灼烧脚部和头部、将点燃的蜡烛放入口中、让他们穿上吸满醋的马尾毛织品“好剥下他们的皮”等等。
另外一个女性被扒光衣物赤身裸体,放在一块冰冷的石头上,再盖一张粗砺的毛织物,就这样放了28个日夜,只喂她些水和面包。
记载此事的日志作家们还说,“法官们下决心过问此事,下令查明相关警长、官僚和行刑者是谁,以便为此等暴行向他们追责”。
作为16世纪最深刻的西班牙学者,胡安・路易斯・维乌斯(Juan Luis Vives,1493—1540)首先发出谴责的声音。
这位西班牙人曾斥责这样的酷刑为“无用而且灭绝人性。”
这个时代的另一怀疑论者蒙田(Montaigne),也毫不犹豫地给它盖上了“本人所反对之事”的大印。
蒙田(1533-1592年),是法国人文主义思想家和文学家,30多岁开始隐居法国乡村(后来曾被迫担任公职),致力研究和写作。尤以其典雅旁征博引的散文著称。
他说:“说实话,这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危害性的方法;为了逃避如此深重的苦难,我们有什么不愿意说、不愿意做的呢?由此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当一个法官为了不致使无辜之人冤死而对囚犯用刑时,他却会用酷刑将无罪的囚徒置于死地……为了避免此人无辜受戮,而对他施加比死刑更严重的伤害,难道有何公正可言吗?”
蒙田进一步借傅华萨(Froissart)的一个故事闻名了自己的立场。
故事讲的是,一个老妇人向巴雅泽(Bajazet)控诉一位士兵抢夺她的粮食。面对被告者的否认,土耳其首领立刻割开这名士兵的胃查看。他被证明有罪。——但是,如果他是无辜的,后果岂不是不堪设想?
1624年,博学的约翰・格拉夫在他的《法庭改革》(Tribunal Reformatum)一文中极力主张将酷刑废除。

就像他所说的那样,他有亲历荷兰加尔文派教徒迫害阿米尼乌斯派(Arminianism)的恐怖经验,而且他的书受到了充分的瞩目,多次重印。
1657年,弗里德里希・凯勒(Friedrich Keller)在斯特拉斯堡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trasbourg)发表了一篇论据充分的论文,敦促将它弃置不用。尽管在1688年重印时,他给标题加的前缀显示,他基本不敢为这不受欢迎的学说承担责任。
随后,当法国编写《1670年特别法典》时,各地拥有最崇高品性和最大量经验的地方法官们都坚定地给出了他们的意见:酷刑毫无用处,它极少能成功地从被告口中逼出真相,应当被废止。
到该世纪末,学者们开始讨论这一问题。其中最著名的,恐怕要数奥古斯丁・尼古拉。
他所依靠的不是辩驳技巧,而更多地是以热忱和学识来驳斥这整个制度,特别对它在巫术案件的适用加以批判。
1692年,冯博登的著作中也提到了此事,并猛烈抨击其滥用行为,不过,还是承认它在许多种案件中的用处。
不久之后,拜勒(Bayle)在他的《字典》(Dictionary)中用他惯用的含沙射影方式谴责了酷刑的存在。
1705年,在哈雷大学,波美拉尼亚的马丁・伯哈迪,一位博土学位的候选人,在他的就职论文中,大力主张将其废除,而其院系主任克里斯蒂安,托马斯(Christian Thomas)称其言之有理,尽管对迅速变革的可行性表达了怀疑。
伯恩哈迪声称,在他所处的时代,荷兰已不再采用它,而对于在乌特勒支地区废除,他认为归功于这样一个案件:

一个盗窃犯在依例受刑并招供时,诬赖了一位鞋匠,就只是为了报复这位鞋匠曾拒收了一双靴子,最后导致其被处死。
伯恩哈迪冒险地用果断决绝的言辞斥责这种制度。
然而,他的主张太过宽泛,实际上直到1798年建立尼德兰共和国时,这种做法才被正式废除。
原文标题:在欧洲立法史上最早谴责酷刑的人是谁
原文来源:立法网微信公众号
(立法网 /编)



 立法钩沉
立法钩沉






 在线客服
在线客服 服务热线
服务热线 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
 top
top